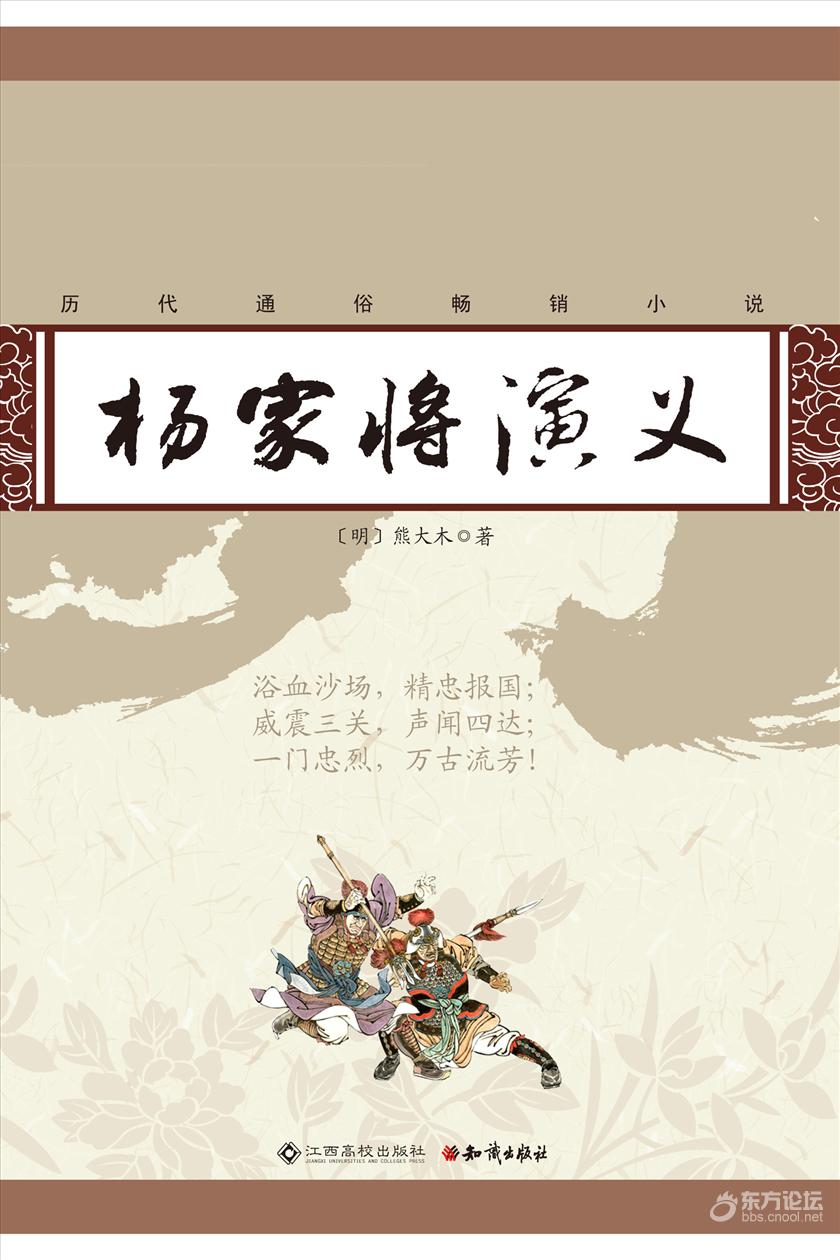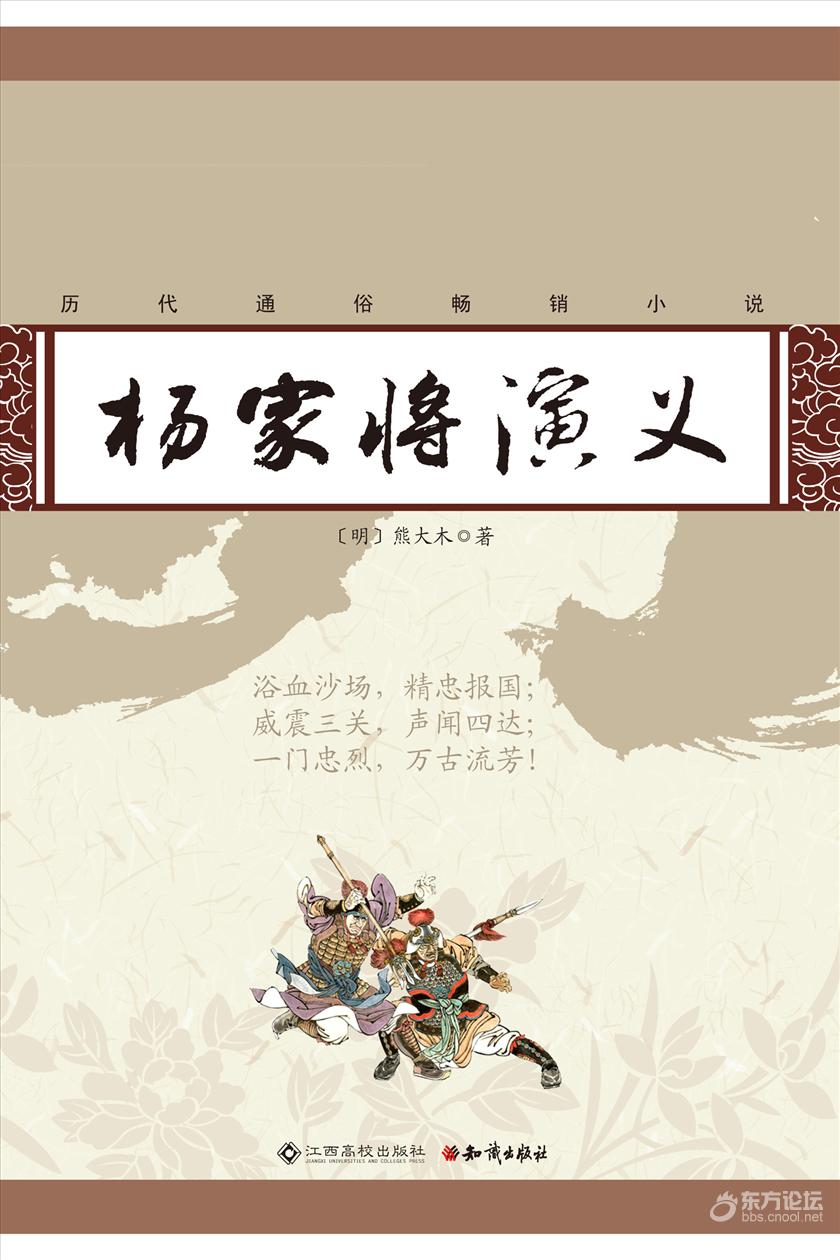

那年暑期的一天,我遇见邻家阿裕,问他:“阿裕,放假好多天了都没见你,去哪儿了?”
阿裕说:“我上半日大多在家里的后间看书,下半日去大茂里听书。”
他又说:“说书先生是亚浦人,说书很不错,是大茂里请来的。”
“要收钱吗?”我问道。
“对小人不收钱,但禁止讲话、吵闹。”
书场设在大茂里的堂前间,正中摆着一张撑板桌,桌上放着一壶茶和一只茶杯,桌后有一张竹椅。中饭后不久,知了在屋前的大楝树上正使劲扯着嗓子,唱着酷暑里特有的情歌。堂前间很阴凉,穿堂风裹着陈年木香,二十几个老人摇着蒲团扇,竹椅在青石板上蹭出吱呀的声响。我和阿裕没带凳椅,就靠着屋柱,脱下木屐垫屁股,坐在堂前的石板地上。
下午一点左右,说书先生来了。他中等个儿,圆圆的脸,一双不大的眼睛,理着板寸头,头发已花白,约五十多岁年纪,可惜腮帮有点瘪,估计掉了几颗大牙。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纺绸衫,下着一条黑色的香云纱裤,脚踏一双牛皮凉鞋,显得比较干净利索。说书先生抖开纺绸衫的下摆,落座后也不客套,戴上老花眼镜,从随身包袱中取出一本线装竖版古书,打开书后,端起茶碗时小指微翘,杯沿在瘪陷的腮帮上压出个月牙印。他先呷了一口茶润润嗓子,然后就开始说起书来。惊堂木拍落,檐角扑簌簌震下几缕积年的蛛网。
先生说的是《封神演义》的第一十六回《子牙火烧琵琶精》,“话说子牙在牡丹亭里,见风火影里五个精灵作怪,子牙忙披发仗剑,用手一指,把剑一挥,喝声:‘孽畜不落,更待何时!’再把手一放,雷鸣空中,把五个妖物慌忙跪倒,口称:‘上仙!小畜不知上仙驾临,望乞全生,施放大德’……。”书到中场,先生去了一趟厕所,休息了十来分钟后,紧接着说第一十七回。这一回说完后,他给听众留下了一些悬念,并以“且听明日分解”结束了当天的说书。
这一年和第二年的暑假,我几乎天天与阿裕一起去大茂里听书,《封神演义》里那些腾云驾雾的神将,已在我俩热血的心里烙下了七十二变的热望。但第三年就没人在大茂里说书了,听说是没人资助。
大约从我读小学五年级开始,柴桥书场搬到了我家附近的镇文化站。书场在晚饭后六点钟开始演出,要买票,由艺人余宝福、虞有富、张亚琴等轮换巡回演唱宁波走书,听书的人较多,约有四五十个。
宁波走书一般由二人搭档演出。演唱者与伴奏者分坐戏台中的长方形茶桌两旁,使用宁波话说唱,词句通俗易懂,说唱并重,并辅以形体动作加以渲染。戏台上的桌子饰以紫红丝绒制作的精致桌围,上面绣“镇海曲艺队“五个金字,桌上放置一把折扇、一块手帕、一块惊堂木。演唱者坐在桌子左边,伴奏者坐在右边。伴奏乐器主要有扬琴、二胡和三弦,曲调丰富多彩,颇具特色。演员除说、唱、弹外,在表演中还串演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多种角色,表现的各种动作引人入胜。余宝福的说唱在扬琴叮咚中如甬江潮涌,张亚琴描着吊梢眉,水袖甩开便是千军万马。最爱看虞有富扮佘太君,龙头拐杖在青砖地上跺出火星:“杨门儿郎何在!”满场的葵花籽都忘了嗑。
镇文化站大门楣下悬起盏红灯笼,阿裕和我常在晚饭后去书场蹭看白戏。起先一段时间,书场检票的是位黑脸大叔,看起来很凶,其实人可好了,一般在书场开演二十分钟左右,就会放我们几个泥鳅似的半大孩子溜进书场。后来不知什么原因,书场检票的换成了柴桥宁远堂的秀珠姐,那就更好说话了。
我有幸在柴桥书场蹭听了二年暑期的宁波走书,比较完整地听过《杨家将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等曲目。后因“文革”的祸害,柴桥书场也被关闭了。
而今经过老戏台遗址,耳畔犹闻檀板声急。当年蹭书的孩子在人生戏台上跌打大半生,每遇困厄,总想起《杨家将》等古书话本里的英雄人物,骨子里从小就有“好男儿志在四方”的烙印,这或是人性中最可贵的不折不挠的一面,在五六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中,不管什么样的困难,都没能压垮我,“逢山开路,遇水搭桥”,一直至今仍是这样。
浙东西蜂 2025年7月28日